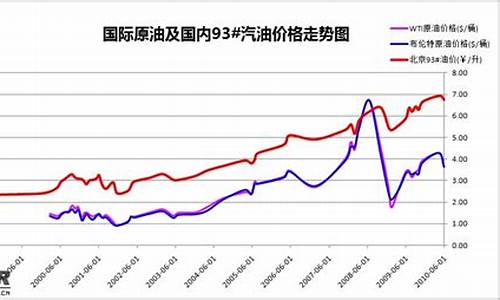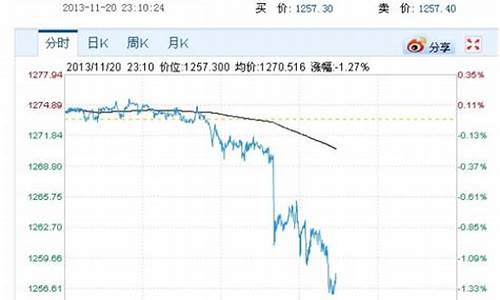开口笑金品50度多少钱一瓶_开口笑帝王金价格
1.诗词:贺新郎·读史
2.于晴《南临阿奴》全文
3.贺新郎读史表达的感情
诗词:贺新郎·读史

原文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
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蹻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
东方白。
注释
人世难逢开口笑:唐杜牧《九日齐山登高》有“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语出《庄子·盗跖》,“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伤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
盗跖(zhi2)庄蹻(jue2):盗跖是春秋战国间的大盗;庄蹻是战国楚人,《荀子·议兵》,“庄蹻起,楚分而为三四”。
陈王: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
黄钺(yue4):象征帝王权力的用黄金装饰的斧子。《书·牧誓》,“王左仗黄钺,右秉白旄以麾”。
译文
与猿拱手作别进化到了原始社会人类犹如呱呱坠地,再经过磨石为工具的石器时代人类进入了少儿时期。炉中火焰翻滚,那是青铜时代,也经过了几千个春夏秋冬。纵观历史,也如人这一生多半忧愁少开怀。尽是征战杀伐弓箭疆场。这大好河山哪一处没有战争没有流血。
一部历史读罢,我已满头白发,我自己的人生也走到了暮年。回顾起来不过是那些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什么王侯将相功名利禄,有多少人为其白首执迷。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难道是真风流?我看不尽然。盗跖、庄蹻、陈胜、吴广这些敢于揭竿而起挑战统治者的权威的人,那才是真豪杰。
赏析一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写这首词时,正在读司马迁的《史记》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篇》。是以史入诗,又以诗论史的。通篇体现历史的唯物主义史观,形象地表现关于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进程。在如何看待中国先秦古史上,作出诗的回答。
“人猿相揖别”,诗从劳动创造了人写起,然后伸展到石器时代,论其生产力是“小儿时节”。虽然经历了二三百万年,但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几千寒热”。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阶级矛盾上升,人们再也难以笑脸相迎,有的是刀光剑影,“流遍了,郊原血”!词的上片,以历史发展为主线,边叙边议。“一篇读罢头飞雪”,下片起句不凡,既有寓意又有气势,承上启下很自然。作者在下片写了一连串上古人物:“五帝三王”、“盗跖”、“庄屩”、“陈王”等,并一一评说,作者用意是宣扬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歌未竟,东方白”,仿佛奇峰凸起,是全诗点睛之笔:天亮了,历史揭开新的一页。
读史、论史这类诗,是很容易写得干巴巴或高深莫测的,然而,写来深入浅出。作者选取的是人们较为熟悉的历史和历史人物,这就拉近了读者与历史的距离。作者还注重把叙史、论史与抒情融为一体。或换言之,是以浓情的笔触写史。“诗言志”,诗的本质是抒情的,诗最终是以情动人的,《读史》的成功秘诀在此。
首句“人猿相揖别”是“平平平平平”句式,有别于《钦定词谱》、《词律》等“[仄]仄平平仄”的定格句式。
诗中“不过几千寒热”,按词谱应是七字句(作上四下三或上三下四);对词谱的个别句子可以添“衬字”,却不可减字。据此,赵朴初先生认为此句脱落一字,建议改为“不过(是)几千寒热”。我们不必认为此句脱字是“创新”,进而求证脱字的微言大义!此词未经审定,由后人发表,笔误应改,这才符合以严肃态度发表诗词的初衷。
赏析二《贺新郎·读史》这首词,正如题目所标明的,是以历史为题材的。当然,不是为读史而读史,而是为了“古为今用”,为了教育今人。这首词的中心思想,它的一以贯之的主线就是阶级斗争观点。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首词就是这番话生动、形象的写照。
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有流血的武装斗争,也有不流血的思想斗争。回顾1964年国际国内斗争的尖锐形势,《读史》一词的写作时代背景是很清楚的,不是无所为而发。这些斗争虽已成为陈迹,但在作者看来,阶级斗争并未停息。重新温习阶级斗争的历史,便是这首词的创作初衷。
诗词一个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概括性强。这一特点,在《读史》上表现尤为突出。仅用一百一十五个字,便囊括了、咏叹了以中国历史为主体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从人类诞生到归宿,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跨度长达几百万年。真是“大笔如椽”、“笔能扛鼎”。
先从词的上阕说起。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这三句是写人类起源和人类历史最初出现的原始社会。世界上原没有什么人类,是劳动创造了人的双手,从而也就创造了人类本身,由类人猿进化为类猿人、猿人、原始人。“人猿相揖别”,便是从猿到人的一种形象化说法。揖别就是拜别,表示珍重。虽不必实有其事,但写得合情合理,恰到好处,不能用其他什么“别”来替代。这首句五个字,飘然而来,用以写人类的从无到有,风调尤觉十分相称,应是诗人的得意之笔。“几个石头磨过”,喻指石器时代。“石器”原是考古学名词,把它还原为自然形态的“石头”,这就冲破了这一专门名词对创作所带来的局限,大大地开拓了词句的容量。因为无论是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也不管是打制石器还是磨光石器,总而言之,都是“石头”。这样,就把长约二三百万年的整个石器时代纳入六字之中了。“小儿时节”,也是个比喻的说法,指人类的童年时期。
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致陈毅》)我以为这三句便是最好的范例。它全是用的形象化的“比兴”,而不用直说的“赋”。因而能以小摄大,举重若轻;以俗为雅,亦庄亦谐;如话家常,别饶风趣,给读者以巨大的美的享受。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这是写人类历史开始由原始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这是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残酷的阶级斗争也就从此开始。“铜铁”两个字,标志着两个不同的时代和社会:铜指铜器时代的奴隶社会,铁指铁器时代的封建社会。冶炼术是个了不起的发明,“铜铁炉中翻火焰”正是写的这一壮丽场景,使我们不禁联想起李白“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诗句。“为问”犹请问,诗词中常用。“猜得”犹猜中,谓作出结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究竟始于何时,史学界迄无定论。关于后者,尤诸说纷纭,竟有西周、春秋、战国、秦统一、东汉和魏晋等六种之多,所以说“为问何时猜得”。这是朋友间相互讨论时的一种风趣说法。它表示的,不是轻易而是亲切。据写于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原是一个西周封建论者,如果有同志一定要问为什么说“猜”?他老人家满可以回答说,我自己不就是这“猜”的行列里的一员嘛!“不过几千寒热”,是说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一时作不出结论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横竖不过几千年罢了。按《词律》,这里应为上三下四的七字句,所以赵朴初同志说可能是在“不过”二字下脱落了一个“是”字,“是无心的笔误”(见18年10月号《诗刊》)。我不以为然。首先,的真迹俱在,这句写得清清楚楚,无任何涂改迹象。下句的“开口笑”的“口”字脱漏了,但当即作了郑重的添补,未必上一句有脱文就不会觉察。这和一贯提倡鲁迅先生说的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的精神也是不符合的。第二,《贺新郎》一调原有一百一十四字、一百一十五字和一百一十六字三体。写于1923年的《贺新郎》便是一百一十六字体。这一首虽少一个字,仍自成一体,在词谱上是允许的,不必添字。第三,从艺术角度看,“不过几千寒热”,语健而气足,作“不过是”便显得不那么紧凑。因此,我以为这不是“无心的笔误”,而是有意的精简。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历史是无情的。伴随着阶级的出现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残酷的阶级斗争。这第一句是用杜牧的诗句:“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九日齐山登高》)但改“尘世”为“人世”,便包括了整个社会。杜牧所抒发的不过是个人的失意寡欢,而感叹的则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悲剧。由于不断的阶级斗争以及各个民族之间的斗争,诸如“血流漂杵”、“积尸成山”、“盈城”、“盈野”这类记载,历史上多得很,真令人不忍卒读,更何来“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是对当时战争的一种典型性的写法。弓箭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武器。“弯”就是拉或挽。弓未拉开时像弦月或者说新月,拉足时又像满月,所以前人多将弓和月合写。李白诗“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塞下曲六首》之五),又辛弃疾词“小桥横截,缺月初弓”(《沁园春》(迭嶂西驰),便是写的未拉开的弓;至于苏轼词“会挽雕弓如满月”,则已明言是指拉满了的弓。“弯弓月”,也就是说把弓拉得像满月,因为这样射出去的箭才更有杀伤力。押韵,是古典诗歌在形式上的首要环节。尤其是律诗和词,还有硬性规定,丝毫不能通融,所以唐宋以来有所谓“险韵”或“剧韵”之说。这种险韵往往是逼出来的,碰到必须押韵的地方,苦思冥想地冒险(其中往往即有创新)。押得好时,便能化险为奇,收到如韩愈所说的“险语破鬼胆”的艺术效果,而作者自己也将有一种如李清照说的“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壶中天慢·春情》)的快感(当然,押得不稳,那便成了所谓“凑韵”)。这里的“弯弓月”便是险韵。非大本领、大手笔,不能也不敢在“弯弓”之后押上一个“月”字。“弯弓月”三字很吃紧,表现了阶级斗争的主题,是下文“流遍了,郊原血”的张本。“流遍了,郊原血”这六个字,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的高度概括。“郊原”二字不是随便用的,因为那正是生产粮食以养活人类的肥沃田野。所以,杜甫也曾痛心地写过“有田不种今流血”这样的诗句。
词的下阕,紧接上文。作者进一步指明读史的方法,要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对待历史人物和,不要让古人牵着鼻子走。上阕基本上是敷陈其事,不置可否,而下阕则是议论,爱憎分明;上阕基本上是不动声色,而下阕则是情绪激昂,大声镗鎝,上下之间的表情是很不相同的。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这一句,在结构上占有重要位置。在词的创作上有所谓“过片”。“片”即“阕”,“过片”就是由上片过渡到下片,也就是下阕打头的第一句。词论家认为这一句要写得如“藕断丝连”,又如“奇峰突起”,使读者至此精神为之一振。我们现在很少填词,但这种不失为经验之谈的言论对欣赏仍不无帮助。这里的“一篇读罢头飞雪”,就是一个兼二者而有之的绝妙“过片”。读到这一句,不禁使我们猛吃一惊:什么原因,一篇读罢竟然使得诗人如此悲愤,不仅头白如雪,而且这如雪的白发还仿佛要飞了起来上冲霄汉?大家全熟悉,是曾以“江山如此多娇”这样壮丽的词句歌颂了我们祖国大地的。然而恰恰就是在这样美好的祖国大地上“流遍了,郊原血”。从“铜铁炉中翻火焰”以后几千年来,不管是奴隶、农奴还是农民又都处于一种被奴役、被剥削的境地。试想,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热爱祖国的伟大诗人,读着这样一部人民血泪史,能不“忠愤气填膺”吗?把“头飞雪”仅仅归之于我国史籍的浩繁,读上一遍,白了人头,是不够的,不够阐明“飞”字所蕴涵的作者的精神面貌。“斑斑点点”是指的个体文字,但似具有双重性,是文字,也是血泪。读到这两句,使我们不由地想起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借狂人之口所说的那几句话:“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这几句是揭露、批判统治阶级唯心史观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历代帝王却把一切创造发明都归功于还处在石器时代的传说人物“三皇五帝”,并说得神乎其神;而历代御用文人又加以吹捧,读史者复无史识,不知是诈,结果是“骗了无涯过客”。“过客”就是指人,人们来到世上,各自走上一趟便回老家,正有似过客。“无涯”一词,出自《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智)也无涯。”可兼指时、空两方面说。“无涯过客”即无穷的过客,极叹受骗者之多。按照自然法则,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过客,但我们不能机械地把“无涯过客”理解为所有的人们,因为也有少数不受骗的。如下面就要提到的盗跖,就曾指着“言必称尧舜”的孔子的鼻子反问:“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庄子·盗跖篇》)陈胜也根本不相信帝王“应天受命”那一套,公然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如果联系陈胜以后出现的历史上无数次大小农民起义和众多的起义英雄,问题就更清楚了。我们所能肯定的是,这里的“无涯过客”是个贬义词,所指范围似甚广,包括自以为能读史而其实并未读懂的所谓“知识里手”在内。关于“五帝三皇”本身,我们不去多纠缠,但想借以说明一个问题。据历史传说,三皇在五帝前,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也是说的“自从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为什么这里却倒过来说“五帝三皇”?这是一个前面已提及的“律诗要讲平仄”的问题。这句七个字,前四个字必须是“仄仄平平”,用“五帝三皇”正合适,用“三皇五帝”就犯了律,绝对不允许。如七律《送瘟神》“六亿神州尽舜尧”,也是为适应平仄和押韵的需要而将尧舜倒转为“舜尧”的。这类情况可以说是律诗所享有的一种特权,是千百年来大家认可的。“有多少风流人物?”这个问话句,在全词中是一转折点。由批判转入歌颂,诗人的心情也由激愤转入愉悦,由“头飞雪”转为“开口笑”。这一句束上起下,一般都将它属下,和上下两句结合在一起,但我觉得还是属上较好。
“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这两句就是对奴隶起义、农民起义领袖的大力歌颂,读者至此亦不觉为之眉飞色舞。盗跖是春秋时鲁人,《庄子·盗跖》篇说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荀子·不苟》篇还说盗跖“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但这些都不能天真地看作是当时学者们在为盗跖说好话,荀子就是把盗跖作为“名不贵苟传”的反面人证的。庄蹻是战国时楚人,楚威王时率众起义。楚分而为四后,他率众至滇池(在今云南),并王其地(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后人遂将他们连在一起作为“穷凶极恶”的标本。如晋葛洪《抱朴子·塞难》:“盗跖穷凶而白首,庄蹻极恶而黄发。”这简直是恶毒的诅咒。但也从反面证明他们的大得人心,所以能“横行天下”、“名声若日月”,并得寿考善终。“流誉”犹流芳。继盗跖、庄蹻之后起义的是秦末的陈胜(即陈涉),规模更大,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大起义,被推翻的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帝国——秦王朝,所以豪情满怀地写下了“更陈王奋起挥黄钺”的词句。陈王即陈胜,起义后得到豪杰们的拥护,都说他“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见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有同志说陈胜“自立为王”,不确;还说之称为“陈王”,意在暗示农民革命为什么总是陷于失败,亦似欠确,未免求之过深。司马迁在《世家》里称陈胜为“陈王”而不名者不下一二十处,在这里利用了这一古已有之的称号,并未如有人所说的暗含什么讥意。“黄钺”,是以黄金为饰的斧钺。作为封建权力的象征,原为帝王所专用,如《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以黄钺斩纣头”。这里说“陈王挥黄钺”,是一种有意识的“反其道而行之”的说法,也就是歌颂。“陈王”非他,即一“辍耕而叹”之贫雇农陈胜是也。
“歌未竟,东方白。”这是一个语带双关、意在言外的结尾,真是“看似寻常最奇崛”。它具有写实与象征的双重性,从写实角度看,是说我这首《读史》的词还未写完,但东方已发白。日理万机,为国操劳,经常通宵达旦,这个结尾便是无意中给我们留下一个活生生的纪录镜头。写这首词时,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从象征的角度看,则是说,对“陈王”以后那许多同样可歌可泣的起义英雄我还没来得及一一歌颂,而中国革命已告胜利了。这样一来,就把两千多年前的农民起义和今天的中国革命很自然地焊接在一起。不仅结束了人类历史上黑暗的过去,而且把我们引向遥远的光明未来。有同志把“东方白”还原为象征“陈王”的起义,并说正是由于这一起义,东方的中国出现了亚洲的黎明,推翻了秦帝国,出现了两汉创造的灿烂的封建文化,这说法很值得商榷。它不像个结尾,也根本结不住这样一篇《读史》,有似悬疣。非常明显,这里“东方白”的“白”,和《浣溪沙》“一唱雄鸡天下白”的“白”,都是象征中国革命的胜利的,不能作别的理解。其区别只在,后者属于“索物以喻情”的“比”,因写作的当时是在丰泽园的灯下;而前者则兼属于“触物以起情”的“兴”,因为写成时正当东方发白,是所谓“兴而比也”。清人沈德潜评李白的七言绝句说:“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令人神远。”这对我们领会这首词的结尾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有启发。
赏析三我们都知道诗人一生酷爱读书,尤其是中国历史书,古典文学、哲学等,无不一一广博涉及。《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又是他百读不厌的着作。他不仅自己爱读书,也爱与别人谈书,叫其他高级干部也要多读书。
从青年时代起,他就与书结下不解之缘,他曾对斯诺回忆说:“我订了一个自修,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饭。我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着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和古希腊的故事。”(引自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第120页)
有关读书的佳话及故事很多,有关他到底在读什么书已成为当时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极欲了解并仿效的头等大事情。我就曾在70年代末期,在广州一名高级干部家里目睹过这样的情形。他书房里的藏书几乎全是历史书,所读之书都是喜欢的书。而他的儿子,也是我的朋友,却偏爱读西洋文学。
上阕起笔就是“人猿相揖别”,说出人类刚诞生时那惊心动魄的一刻。但表面写来却是那么轻松,好像只是人与猿作了一个揖就从此分道扬镳了一般。这个“揖别”用得极为形象,而富有谐趣,但“人猿”却显得很巨大,富有深沉遥远的历史感,两个词汇一搭配,诗意立刻就产生了,读者的心也一下被震荡起来了。
接着是漫长的人类的“蒙昧时代”,几百万年就这么过去了,这就是人类发展最早的阶段——石器时代。这个时代在诗人眼中不过是磨过的几个石头,仿佛只是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的儿童时代。一个“磨”字让人顿生漫长而遥远之感,而“小儿时节”让人感到诗人对人类的把握是那么大气又那么亲切,这一句有居高临下之概,也有往事如烟之叹。
第四、五、六句,诗人仅用了三句就交待了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入了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铜铁炉中翻火焰”一句写得既形象又浓缩,仅此一句就把火焰中青铜之光的象征意义写出来了,人类随着铜与铁步入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但若要问这一具体时间,却不易猜得确切,不过也就是几千年的春夏秋冬而已嘛。时光在飞逝,时光在诗人的眼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并不足道,仿佛眨一下眼就过去了。
“人世难逢开口笑”一句化用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中一句:“尘世难逢开口笑”。但诗人在这里化出了新意(此句本意是指人生欢喜少悲伤多,也就是哭多笑少,恨多爱少),在此句中注入了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含意,正如诗人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所指出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面对如此严峻的斗争,人生当然难逢开口笑了。而且还不仅仅是“难逢开口笑”;还要在人生的战场上一决生死,剑拔弩张,这是指具体的生死存亡的阶级斗争,是指革命是,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而结局呢?那自然会有牺牲,会有鲜血。人类的历史充满了血腥与残杀,诗人在此喟叹出二句:“流遍了,郊原血。”鲜血只能不断唤起革命者的斗争,革命者面对鲜血岂能笑得出声来。
下阕第一句非常富有诗意,用一句“一篇读罢头飞雪”就艺术性地浓缩了诗人自己一生读历史书的情形。诗人从少年到老年一直潜心读史,不知不觉一下就满头青丝变白雪了。这句诗也透露了诗人对人生、对历史的感慨,真是人生易老,一刹那青春即逝,转眼就是暮年。
那么对于中国浩瀚的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能让人记得些什么呢?诗人仍从一贯的大象着眼,举重若轻,一笔带过。诗人道:只记得些斑斑点点,那也不过是几行陈年旧事而已,什么“五帝三皇”的神圣伟业,那不过是些骗人的东西,却还骗过了多少人世间匆匆的过客。其中到底有几个真风流人物呢?诗人虽用的问句,但意思却是所谓正统史书上所赞誉的风流人物都是伪风流人物。
在诗人的眼中,真正的风流人物是那些被所谓历史斥骂的人物,如盗跖、庄蹻、陈胜,这些农民起义的领袖,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他们揭竿而起,反抗剥削阶级,是赫赫有名的造反英雄。
最后二句,诗人沉浸在吟咏历史的情景中,歌声意犹未竟。当诗人终于拨开历史的迷雾,剔除了伪英雄,找到了真英雄时,不觉已是东方曙色初露了。这“东方白”一句,有二层意思,一是指诗人吟咏此诗直到天亮,犹如李贺《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诗中一句:“吟诗一夜东方白”。二是喻指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历史谱写了新篇章,犹如旭日东升,势必光华万丈。
其他优秀文章:
于晴《南临阿奴》全文
1
今日南临年后第一场宫宴,朝中重臣家眷尽数应邀出席。
南临徐家也在其列。
「原来,那就是徐五长慕吗?」各自家眷窃窃私语。
「他长得一点也不像徐六,更不像徐老将军啊。」
「莫不是代养的遗孤吧?他家徐四定平不就是如此?」
「不不,听说他是私生子,母亲是南临劣民,才会相貌平平,他这种相貌的人几乎没在南临见过了。」
「那《长慕兵策》真是他少年写的?不是说,劣民生下的孩子才智都不高么?是不是谁代的笔?」闲话的女子吓得住口,徐家席上有个女娃儿龇牙咧嘴地瞪向她们这头。
这么远,又有丝竹之音,怎么听得见她们这头的闲话?
那女娃儿,正是徐家幼女徐烈风。她年仅十岁,与一般俊男美女的南临人相同,幼年已可窥见将来美丽的貌色,她恨恨嗤了一声,低骂道:「什么东西!」
「阿奴,什么东西?」身边的少年问道。
她连忙转头,讨好地朝他说道:
「五哥,是陛下赏赐的果子,轮到咱们这桌了。」此次徐家参加宫宴,只有爹、五哥跟她,其它兄姐尚在边关未归,有官职的都在另一头,这头都是家眷。五哥眼力不太好,她立刻起身代为接过公公赐来的水果。
「多谢公公。」她道,语气却没有多少敬意。
徐长慕半垂着眼睫,没有纠正她的态度。
那年岁颇大的公公笑道:
「陛下说了,今日徐家烈风可爱至极,他老人家看了心情甚是开怀,要咱家多添些瓜果给六**,但咱家怕选的不合六**口味,不如六**自己挑吧。」
徐烈风闻言,满面开心笑道:
「陛下圣恩,烈风领之。」她想了想,专门挑上五哥爱吃的瓜果。
邻近的家眷,耳尖的俱是一惊,纷纷往她这头看来。陛下宠爱徐家第六女,朝臣都是知道的,家眷间也有流传,但,他们不知居然宠到可以由她自行挑选陛下的赏赐。
先前他们目光全落在那个争议颇大的私生子徐长慕身上,现在定睛一看,此女今日穿的不是代表徐家的白色,而是一袭黑色衣裙,上有金线绣纹。众人微地动容,金色?那不就是皇室的颜色?也是陛下赐的?
徐烈风未觉他人心里的惊异不定,在昏暗的烛光下扫过陛下那方向。宫宴是在晚间,依距离是看不清陛下的面容,但她眼力甚好,一眼就清楚地看见陛下,以及陛下身边的皇子萧元夏。
萧元夏只比五哥小上一岁,与她却是十分友好。她自幼三不五时就被陛下召见,连带着,也时常得见陛下身边的大凤公主与夏皇子。
人的感情就是如此,看顺眼的就凑在一块。她看萧元夏十分顺眼,顺眼十分,于是他俩成了铁哥儿们的交情。
萧元夏正看向她这头,她立即露出灿烂的笑容。萧元夏掩嘴轻咳一声,虽然看不清她这头五官,但也知道她冲着自己直笑,一想起她平日开怀的笑容,他面色微红,转过头去。
过了一会儿,他再转回来时,已见她异常亲爇地喂着徐长慕。
他眉头轻皱,心里想着:小烈风对她五哥很是喜欢,徐长慕眼力也不好,如此喂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他控制不住,心头隐隐对徐长慕起了厌恶之意。
「五哥,好吃么?」她问着。
「挺甜的。」他平淡道:「阿奴,我视物只是模糊,还不至于看不见,我可以自己来。」
「不不,现在我是五哥的眼,是五哥的手,等你成人礼后,就用不着阿奴,阿奴现在当然要好好服侍五哥。」很甜?她嘴贪,悄悄就五哥那一口咬了下去,果然饱满多汁,这到底要说陛下赏赐得好呢,还是她徐烈风太会挑了?
「……谁跟你提到成人礼的?」
「我听见三哥说的。他们说,因为五哥是……等你过了成人礼,就能清楚看人,长相也会变得跟大哥二哥三哥他们一样好看。可是,我觉得五哥现在就很好了。」她有点害怕,怕他一旦变了个样儿,就跟其它兄姐一样,对她有着隐约的敌意。
思及此,她又亲昵地凑过去,巴不得坐进他怀里,让他感觉她的善意、她的尊敬,以及对他的喜欢,不要哪日不需要她了就拒她于千里之外。
「我跟五哥很要好的,是不?五哥叫阿奴做什么,阿奴都做的。」她低声说着,紧紧抓着他修长的手指。
徐长慕拿出帕子,反拉过她的手指慢慢擦着。他漫不经心笑道:
「你觉得我真好?」
「当然,五哥内外俱好!」她真心诚意地说着。
他笑出声。「内外俱好?亏你也说得出来。」
「五哥莫要妄自菲薄。你年方十六,就已经为南临写出兵策了,如今边关徐家将领都奉《长慕兵策》上册为宝贝,一日三读,就连宫里也收着《长慕兵策》下册,都知道你是南临第一天才,称你一声南临长慕,阿奴实在不知天下还有哪一人比得上我五哥?」她无比骄傲,又笑嘻嘻地抢过他手里帕子,帮忙擦他沾着瓜果甜汁的修长手指。她偏头望着他,轻轻点了下他眼角的泪痣,细声道:「至于面貌,在阿奴心里,五哥现在就很好了,真的,阿奴就喜欢五哥这样,就喜欢五哥的泪痣,就算你一辈子都不成人礼,阿奴也愿意陪在五哥身边,当五哥的眼手。」
他眼睫动了动,往她看去。
他轻轻眨眨眼。她的面容还是模糊一片,但完全感受得到她两道爇情的目光毫不保留地直落在他的脸上。
「五哥,如果你真想成人礼……那阿奴也是可以帮你的。」她勉为其难道,心里直盼着他一生就这样好了。
徐长慕一噎,马上淡定道:「阿奴你……知道成人礼是干什么的么?」
「当然知道。」她凑近到他耳边,道:「男女同房,阴阳调和,乾坤交融,因人而异,少则一日,多则三日才能完全结束,我瞧五哥是南临第一天才,说不得要七、八日才能完成,所以阿奴也挺小心的……」
「……小心什么?」他面无表情了。
「难道五哥没发现,这一年阿奴在你床上滚一滚都滚不过一晚上?要滚久了不小心让五哥完成成人礼了,那……」她叹了口气,实在是非常盼望那一天不要到来。
徐长慕的手指一颤,镇定地将这个太过亲近他的徐家老六推开。
「五哥……」她失望至极,很想再赖上去,但他耳垂微红,肯定气炸了。她不敢在此刻触怒他,只好乖乖与他分坐左右。
是哪儿触怒他了呢?她暗暗反省。自幼她跟五哥好……很好很好的,好到就算其它兄姐不喜她,五哥不讨厌她,她也就满足了,他俩好到她可以成天跟五哥厮混,他也没说过一个烦字。
所以,就算五哥过他个千百个成人礼,也不会在成人礼后与她生疏才是。
她心里有点焦虑,正巧与斜角的大臣之子对上眼。那人叫余延显,跟萧元夏同龄,却令她十分憎恶,只要她一在街上遇见他,非团战打到鼻青脸肿不可!尤其近日她心情不佳,下手重了些,此刻看见他,还隐约看见他眼下遮掩的青肿。
活该!她想着。
谁教他父亲老爱上书东扣扣西抠抠,让边关的徐家军过得苦哈哈,抠下来的都塞进自家口袋,偏偏爹严厉地不准她乱说,要不然,她早就揭了余家的底。
她对他露出凶狠狼犬貌。桌上刚赐来一盘油炸鱼,她用力拿筷子在鱼上一戳,挑衅地看着老被她叫油炸鱼的余延显。
那少年面色铁青,咬牙切齿了。
「陛下有旨,宣徐五长慕上前晋见!」
不知何时,歌舞已停,徐烈风立刻起身,小心地托住他的手臂。「五哥,我扶你过去吧。」
「你应对注意些,别把方才成人礼的事说予陛下听。」他道。
「这是当然!」她还怕说给陛下听,陛下要他快快成人礼呢。
在众目睽睽下,徐烈风领着他往殿中间走去。各人心里甚是惊诧,京师里谁不知徐家老六生性骄纵,非但家里纵容她,连陛下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容她在天子脚下胡闹,但现在瞧瞧他们看见了什么?
一头小忠犬规规矩矩,体贴至极地扶着人。
「五哥,要跪下了。」她殷勤说着。
徐长慕应她一声,两人齐齐跪下,齐声道:「陛下万岁。」
高高在上的南临君王回过神,皱起眉头。「徐五长慕?」
「正是草民徐五长慕。」
「你眼睛看不见到需要人扶持的地步?怎么不去寻个丫鬟呢?」
徐烈风瞪大眼,连忙插嘴:「陛下,我五哥现在有我就很好了,何必找丫鬟呢?」
「难道你们在家里都是如此?焦孟不离?让妹如此照顾你?」他微地眯眼。
有何不可呢?徐烈风正想答话,她还巴不得呢!这陛下也管太多了吧!
徐长慕平静答道:「在府里自是各自事各自理。只是今日是陛下盛请宫宴,容不得婢女在宴上冒犯,这才托得徐六帮忙。」
她及时住口,偷觑着五哥。这五哥,谎言说得真是流利呢。
南临陛下嗯了一声,道:
「你抬起头来。」
徐长慕抬起头来,但眼眸半垂,没有直视高殿上的男人。
附近宴席上有人轻轻掩嘴笑着。
徐烈风立即往那头瞪去。
有什么好笑的?有什么好笑的!这是她五哥,又不是他们的五哥,她不嫌就好了!而且她五哥也生得不丑,只是在大部分的南临人里显得稍稍平凡点,居然敢笑他!她又恨恨看去一眼,将那些笑的女眷都记在心里,姓罗的、姓方的……她一辈子也不忘!
她又扫过父亲的面容。父亲也是半合着眼,似乎对那些女眷的窃笑不以为意,她心里更怜惜五哥,一时间只觉五哥跟她一样,都不得父兄疼爱,他俩是一样的同病相怜。
她又往陛下瞪去,准备陛下一开口笑,她就呛回去。
南临帝王嘴巴才张开,就见一双火爆的小美目正杀气十足地瞪着自己,他愣了一下,又拱眉看向那个面貌平淡到令人记不住的徐长慕。坐在身侧的大凤公主呵呵笑道:
「果然世上人无十全十美,徐五长慕才智名动京师,可惜面貌残缺,这等南临劣民之貌实在不好讨上一桩好婚事。父皇,不如您为五公子说个媒,也好让徐老将军安心回边关,是不?徐老将军?」
「臣……」徐将军自那头席后站起。
徐烈风真怕她爹就这么允了,连忙截断他的话,对着大凤公主呛道:
「莫非公主想与我五哥结亲?要不,这般关心他的婚事?什么面貌残缺!我五哥好得很呢!」
「徐六!」徐长慕低声喝着。
大凤公主闻言,美眸抹过几不可见的不悦,勉强笑道:
「徐六妹妹,你忘了么?皇室与劣民之后,岂能结亲?我也是为你五哥好哪。现在的南临劣民已经跟咱们相貌上没什么不同,但在许久以前谁都知道有一批劣民的相貌残缺一如徐五公子,虽然劣民的神话里有提及这些残缺的人,经成人礼后偶有人面貌渐为秀美,近似南临人的美貌,但,这些都是神话,没有一个学士敢出面证实。南临人爱美是天性,如果没有陛下赐婚,也许没有人会……」
徐烈风满腔怒火,大声答道:「谁说南临人都爱美,我就不会……」
萧元夏心头咯噔一跳,神色自然地在旁插话。「父皇,徐五眼力不好,不知是怎么写下兵策的?」
南临帝王瞥了他一眼,哈哈一笑,顺着他的意思改变话题:
「是啊,朕也是很好奇,徐五长慕,你是怎么写下这《长慕兵策》的?」
徐烈风瞪大眼望着上头这对父子。他们不是早就知道了么?
徐长慕状似恭谨地答道:
「长慕口述,徐六代写。」
「你俩真是合作无间哪。」南临帝王看向徐烈风时,笑道:「小烈风年纪尚小,不但写了一手好字,还懂得兄长艰涩的用字,真真了不起哪。」
她沾沾自喜。「都是我五哥教我的!他是南临天才,都叫他南临长慕,陛下,不止我五哥,我上头还有四位兄姐,如今都在边关替陛下守着南临江山,陛下不管要开几次宫宴,或者,哪日从此不早朝了,徐家人都还是陛下的手脚,继续守护南临。徐家忠心,日月可表,若然陛下因为我二娘的身分,而歧视我五哥,那就是南临无可挽回的损失了。」
她字字珠玉掷地有声,本是一场年后去冬的爇闹宫宴,此刻却是静悄悄地,没人敢再说话。
不知从谁开始,喊道:「请陛下息怒。」
哗啦啦的,全跪了。
徐烈风一怔,有点迷惑。她是哪儿说错了?抬眼对上萧元夏,他的脸色却是悲壮得黑了。
萧元夏硬着头皮想开口为她缓颊一下,哪知南临帝王笑声震天,他道:
「都起来都起来,好个忠心小徐六!朕岂无雅量容徐家这点小小的诤言呢?以后朕会好好省这宫宴的。」他看徐五还跪在那儿,笑道:「徐五长慕此时如何想法?」
「盼请陛下恕罪,徐六太过年幼,不知分际,也许是徐家太过宠她之故,若是陛下不喜,徐五必照陛下旨意教导她。」
南临陛下深深看他一眼,似笑非笑道:
「徐家教得很好,朕甚是喜欢她这种性子。南临人多是寒蓄性子,少有像她天生飞扬爇情,更别谈南临大半百姓天生身子骨不佳,她很好,都很好。都起来吧,你也一块起来,要不,这小烈风也跪在那地上,才几岁呢,累着了吧。你过来让朕仔细看看。」
徐烈风得了徐长慕的同意,这才起身小心翼翼扶起她最敬重的五哥。
「五哥,陛下让我过去一会儿。」见他点点头,她一步一回头,确定五哥不会摔倒什么的。
「人就在那儿不会跑。」南临陛下一伸手,将她拉进怀里,笑道:「让朕看看,许久不见的小烈风是胖了还是瘦了?」
「陛下前几日才见过烈风,哪来的许久不见?」
大凤公主靠过来取笑道:
「父皇甚是宠爱你啊!六妹妹。当年我像你这么点大时,父皇对凤儿可不会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呢。」
徐烈风面部微地扭曲。方才她明明与这大凤公主闹得不对盘,怎么公主的面皮都变得极快,转眼可以亲切得像是亲生姐姐一样?
萧元夏对她使了个眼色,叫她哄哄陛下,她一头雾水,软声软气道:「陛下生气么?」
「哈哈,朕对你怎会生气?」他搂着她的身子,任着徐五孤独立在殿中央,取过一颗葡萄送进她桃红小嘴里。
大凤公主见了,眼色莫测,回到她的席后,不发一语。
萧元夏的面色微白了。
「小烈风,今年也十岁了吧?」他笑问。
「嗯,十岁了。」要哄陛下开心么?这她懂。以前她常哄家里父兄开心,可是他们都不买帐,她也取过一颗葡萄送到陛下嘴里。「陛下请吃。」
南临帝王一愣,而后微微一笑,一口吃进去。「怎么你给的都这么好吃?」
萧元夏的拳头紧握。
徐烈风笑咪咪着:「这当然。比陛下给我的还好吃。」
「哈哈哈……」他笑声不断,目光又落在徐五身上。「你哪来的二娘?说给朕听听。」
「二娘是指五哥的母亲。」都这么说着,五哥的母亲是劣民出身,爹是高贵的胥人之后,无法纳她,所以五哥是个私生子,爹也默认了。也正因母亲是劣民,身为劣民之子的五哥,即使写出世上少见的兵策,也是做不了官的。
「你娘从头到尾,也只有一个罢了,喊人家二娘,也得看她承不承得起。」
「为什么承不起……」
「好好,瞧你,就为了你家兄长生朕的气。」他笑着对左右儿女说道:「瞧,他们感情很好哪。」
大凤公主笑道:「父皇,凤儿与夏弟虽是不同母所出,但手足情深不输徐五跟六妹妹这对好兄妹哪。」
南临陛下轻轻哼了一声,又朝徐烈风慈爱笑道:
「小烈风觉得麻烦么?那样细心照顾你五哥,连朕看了都心疼你。你还小哪,是该胡闹玩耍的时候,却要花那心思照顾你那盲……那眼力不好的哥哥,不然,朕替你五哥指个婚?往后就让你嫂子好好顾着他,也省得你人小顾不了你五哥。」
她瞪大眼。「陛下,现在烈风这样照顾五哥就很好了,你可别乱破坏咱们兄妹感情,而且,这婚要是指成怨偶,陛下也赔不起,您还是让五哥自由的相爱,那才是最好的恩赐。」
「自由相爱?小烈风居然也明白了。这徐五,真是指点你不少了。」南临陛下笑声不绝。「那小烈风呢?也想自由相爱?这可怎么好,朕这些年一直在苦思,这南临有哪个人才配得上你,至少,是南临最有权势的人才配得上你啊……」
萧元夏闻言,下意识地看向他的父皇。最有权势的人,那不就是……他心里微微发冷,朝徐烈风又暗打个手势。
他俩一向心有灵犀,她眼波一转,有点诧异,仍依着萧元夏的暗示,答道:
「烈风也要自由相爱,就跟陛下一样。陛下可别胡乱替烈风指啊。」
「跟朕一样?」
「南临一帝一后,三百年来从未有过例外。陛下十六岁时大婚,第一位皇后娘娘走后,才来第二位皇后娘娘,至今,二位皇后娘娘都去了许多年,后位仍是悬空,陛下这不是极喜爱二位皇后娘娘,才忍着十几年的寂寞吗?」
南临陛下一怔,眼底短暂迷蒙,松了怀抱。
萧元夏又暗地对她摆了摆手,要她快快退下。
她道:「陛下,我……」
「你五哥站在那儿也累了,你扶他回去坐着吧。」他淡淡地说着。
求之不得呢。徐烈风行了个宫礼,退回殿中央,看五哥没有气恼之色,这才讨好地摇着尾巴扶着他回宴席。
这对兄妹在宴席间交头接耳。以外貌来说,徐烈风年幼但美貌逼人,完全压制平凡无奇的徐长慕,尤其两人往同一地站去,徐长慕几乎是彻底了,但她在态度上事事以徐长慕为尊,眉目间对他的亲爇出乎一般手足,倒显得主控权在这个平凡的徐五手上。
南临君王凝视良久,朝左右儿女又笑道:
「小烈风真是比南临人爇情许多,对待兄长事必躬亲,感情总表露于外,如果她的兄姐是你们,想必南临皇室定是一片和乐,你俩该学学她的态度。」
「是。」大凤与萧元夏齐声答着。后者往那对兄妹看去,忍不住撇过脸。兄妹么,这烈风有必要亲爇成这样吗?她懂不懂事啊!
贺新郎读史表达的感情
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
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屩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
东方白。
注释
人世难逢开口笑:唐朝杜牧《九日齐山登高》有“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语出《庄子·盗跖》,“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伤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
盗跖(zhí)庄屩(jué):盗跖是春秋战国间的大盗;庄屩是战国楚人,《荀子·议兵》,“庄屩起,楚分而为三四”。
陈王: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
黄钺(yuè):象征帝王权力的用黄金装饰的斧子。《书·牧誓》,“王左仗黄钺,右秉白旄以麾”。
译文
人与猿已拱手作别了。
似乎只磨过了几个石头,
在儿童时代。
后来炉中又翻卷着铜铁的火焰,
如要我猜猜到底为何时?
那不过是几千年的春夏秋冬。
人世间难得开怀大笑,
上战场彼此剑拔弩张。
流遍了呀,
郊原尽是血泊。
读完一部历史书不觉已满头飞雪,
仅记得些零星斑点,
几行陈年旧事情。
五帝三皇的神圣伟业,
不知骗了多少匆匆过客。
到底有几个风流人物?
盗跖庄蹻身后留美名,
还加上陈胜王揭竿而起。
我歌声意犹未尽,
东方已露曙色。
赏析
我们都知道诗人一生酷爱读书,尤其是中国历史书,古典文学、哲学等,无不一一广博涉及。《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又是他百读不厌的著作。他不仅自己爱读书,也爱与别人谈书,叫其他高级干部也要多读书。
从青年时代起,他就与书结下不解之缘,他曾对斯诺回忆说:“我订了一个自修,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饭。我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和古希腊的故事。”(引自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第120页)
有关读书的佳话及故事很多,有关他到底在读什么书已成为当时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极欲了解并仿效的头等大事情。我就曾在70年代末期,在广州一名高级干部家里目睹过这样的情形。他书房里的藏书几乎全是历史书,所读之书都是喜欢的书。而他的儿子,也是我的朋友,却偏爱读西洋文学。
诗人写的这首《贺新郎·读史》就是自己一生读书,尤其是读中国历史书的艺术性的总结,充满诗情画意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这首诗从人类诞生一直写到社会主义,纵贯几百万年的历史,而着墨仅仅115个字,的确是气象恢宏,古今罕见。
上阕起笔就是“人猿相揖别”,说出人类刚诞生时那惊心动魄的一刻。但表面写来却是那么轻松,好像只是人与猿作了一个揖就从此分道扬镳了一般。这个“揖别”用得极为形象,而富有谐趣,但“人猿”却显得很巨大,富有深沉遥远的历史感,两个词汇一搭配,诗意立刻就产生了,读者的心也一下被震荡起来了。
接着是漫长的人类的“蒙昧时代”,几百万年就这么过去了,这就是人类发展最早的阶段——石器时代。这个时代在诗人眼中不过是磨过的几个石头,仿佛只是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的儿童时代。一个“磨”字让人顿生漫长而遥远之感,而“小儿时节”让人感到诗人对人类的把握是那么大气又那么亲切,这一句有居高临下之概,也有往事如烟之叹。
第四、五、六句,诗人仅用了三句就交待了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入了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铜铁炉中翻火焰”一句写得既形象又浓缩,仅此一句就把火焰中青铜之光的象征意义写出来了,人类随着铜与铁步入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但若要问这一具体时间,却不易猜得确切,不过也就是几千年的春夏秋冬而已嘛。时光在飞逝,时光在诗人的眼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并不足道,仿佛眨一下眼就过去了。
“人世难逢开口笑”一句化用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中一句:“尘世难逢开口笑”。但诗人在这里化出了新意(此句本意是指人生欢喜少悲伤多,也就是哭多笑少,恨多爱少),在此句中注入了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含意,正如诗人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所指出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面对如此严峻的斗争,人生当然难逢开口笑了。而且还不仅仅是“难逢开口笑”;还要在人生的战场上一决生死,剑拔弩张,这是指具体的生死存亡的阶级斗争,是指革命是 ,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而结局呢?那自然会有牺牲,会有鲜血。人类的历史充满了血腥与残杀,诗人在此喟叹出二句:“流遍了,郊原血。”鲜血只能不断唤起革命者的斗争,革命者面对鲜血岂能笑得出声来。
下阕第一句非常富有诗意,用一句“一篇读罢头飞雪”就艺术性地浓缩了诗人自己一生读历史书的情形。诗人从少年到老年一直潜心读史,不知不觉一下就满头青丝变白雪了。这句诗也透露了诗人对人生、对历史的感慨,真是人生易老,一刹那青春即逝,转眼就是暮年。
那么对于中国浩瀚的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能让人记得些什么呢?诗人仍从一贯的大象着眼,举重若轻,一笔带过。诗人道:只记得些斑斑点点,那也不过是几行陈年旧事而已,什么“五帝三皇”的神圣伟业,那不过是些骗人的东西,却还骗过了多少人世间匆匆的过客。其中到底有几个真风流人物呢?诗人虽用的问句,但意思却是所谓正统史书上所赞誉的风流人物都是伪风流人物。
在诗人的眼中,真正的风流人物是那些被所谓历史斥骂的人物,如盗跖、庄蹻、陈胜,这些农民起义的领袖,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他们揭竿而起,反抗剥削阶级,是赫赫有名的造反英雄。
最后二句,诗人沉浸在吟咏历史的情景中,歌声意犹未竟。当诗人终于拨开历史的迷雾,剔除了伪英雄,找到了真英雄时,不觉已是东方曙色初露了。这“东方白”一句,有二层意思,一是指诗人吟咏此诗直到天亮,犹如李贺《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诗中一句:“吟诗一夜东方白”。二是喻指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历史谱写了新篇章,犹如旭日东升,势必光华万丈。
[免责声明]本文来源于网络,不代表本站立场,如转载内容涉及版权等问题,请联系邮箱:83115484@qq.com,我们会予以删除相关文章,保证您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