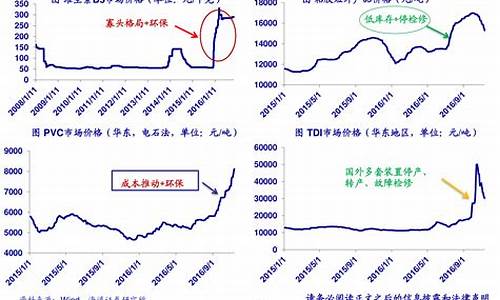铜合金锭价格_龙岩铜合金价格批发
1.2008北京奥运会圣火怎么点燃?
2.龙岩市新罗区适中镇三美楼(凝庆楼)游记
2008北京奥运会圣火怎么点燃?

一.使用什么物质点燃的?
答:燃料用的是99%以上纯度的丙烷历史上的奥运火炬用混合燃料的较多。用丙烷燃料是为了能在火炬传递路线范围内,满足环境温度的要求。其次颜色也是一个考虑,丙烷燃烧后火焰是橙色,具有较好的可视性。且价格低廉,常用,其主要成分是碳和氢,燃烧后只有二氧化碳和水,没有其他物质,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二.如何点燃的?
答:从钻木取火到电子点火,人类取火的方式越来越先进,但是集奥运火种的原理却并不高深,因为只有用传统的方式取火,才能象征奥运圣火的纯洁,象征古奥运会传统的传承。集奥林匹克圣火的唯一方式是利用凹面镜集中阳光,产生高温引燃火种。凹面镜取火的原理非常简单,在我国很多阳光充足的地区也用凹面镜烧水做饭。
圣火点燃后,火种被置于一个古老的火种罐中由首席女祭司带到古代奥运会会场内的祭坛,点燃第一名火炬手的火炬,随后开始它前往奥运会主办城市的行程。
由于设备原理简单,但对于阳光有一定的特殊要求,而且女祭司只有三次集圣火的机会,所以一旦取火仪式当天遇到恶劣天气,就需要更改圣火集时间或用备用火种,备用火种一般在彩排时就已提前集。例如2000年悉尼奥运会火种集的关键时刻乌云密布,导致取火失败,不得已用前一天彩排仪式上取到的火种代替。
三.为啥要由最高女祭祀点燃?
答:这和古希腊的传统有关。在希腊神话中,火是赫菲斯托斯的神圣象征,是普罗米修斯从宙斯手中偷得赠送给人类的礼物。因此在每个古希腊城邦的中心,都有一个燃烧长明圣火的祭坛,而城邦居民每家每户也都有长明圣火,以供奉女灶神赫斯提亚。在古奥林匹亚城的议事大厅有一个供奉赫斯提亚的祭坛,祭坛的圣火是用凹面圆盘或镜面聚焦太阳光点燃的。圣火永不熄灭。凹陷的光滑平面能够将阳光汇集到焦点,最高女祭司将火炬伸到焦点处,就能够将其点燃。
四.如何防止被熄灭?
答: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接力活动将历时130天,传递总里程约13.7万公里。在这漫长的“旅途”中,圣火会在一只只火炬间接力传递。那么我们将怎样保证整个火炬接力过程不出纰漏呢?
首先我们来看火炬,北京奥运会火炬长72厘米,重985克,在工艺上用轻薄高品质铝合金和中空塑件设计,下半部喷涂了高触感塑胶漆,手感轻盈舒适且不易滑落;每支火炬的燃烧时间15分钟,这对于传递过程已经足够,因为每届奥运会火炬手数量和传递距离有所不同,此次传递每天将有208名火炬手参与传递,一般每个火炬手传递200到400米,整个过程不会超过十分钟。
130天的过程中,有33天属于境外接力,5月4日后圣火将回到中国大陆,继续其在内地进行天的旅程。4个多月里,圣火将“光临”我国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113个城市和地区,地理环境差异性较大不说,难保不碰上刮风下雨,火炬的火焰会受到影响吗?
当然不会。北京奥运会的火炬在燃烧稳定性与外界环境适应性方面,达到了全新的技术高度,能在每小时65公里的强风中和每小时50毫米的大雨下保持燃烧,最低零下6℃到最高45℃的温度变化也不会对其燃烧产生影响。据悉,该火炬令人骄傲的内部燃烧系统是由航天科工集团自主设计研发,由于涉及军工技术,火炬燃烧技术被视为北京奥组委的核心机密。
另外,火炬火焰在零风速下火焰高度25至30厘米,在强光和日光情况下均可识别和拍摄,也就是说,不能到达现场为火炬手加油的朋友可以在电视机前看到清晰的火焰。这是因为丙烷产生的火焰呈亮**,火炬手跑动时,飘动的火焰在不同背景下都非常醒目。丙烷是一种无色无味且价格低廉的常用燃料,可以适应比较宽的温度范围,近几届奥运会都用丙烷等混合气体做燃料。
北京奥运会的“绿色奥运”理念在火炬上也能够得以体现。北京奥运会火炬的外形制作材料均为可回收的环保材料,而丙烷作为一种碳氢化合物,在燃烧后主要产生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同样也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龙岩市新罗区适中镇三美楼(凝庆楼)游记
龙岩市新罗区适中镇三美楼拥有非常丰富的人文历史痕迹,这里是闽南文化的重要基地,很多古代的建筑物依旧保留了当初的风格,虽然在特殊时期被破坏和更名,但是现在仍然屹立不倒,下面给大家分享龙岩市新罗区适中镇三美楼游记攻略。
举国欢庆的早晨,阳光朗耀,天蓝云白。乘着长的好时光,卸去紧张与焦灼,装上轻松和愉悦,赶去爱人老家那座古老的“三美楼”赴一场热闹欢腾的团聚,走一趟穿越漫山遍野稻黄橘红秋色的旅行,搜一筐那些越飘越远的先人的尘埃往事。
“三美楼”(时被人硬生生地篡改写为“凝庆楼”)是闽西红土地上万千座土楼中的一座,它方形,三层高,一门三进,矗立于龙岩市新罗区适中镇。镇子是福建的四大古镇之一,古镇安古宅,再也没有比这更自然搭配的事了。
三美楼
暖融融的阳光穿透车窗,洒满我们身上,启亮了心堂,血沸了起来。车轮下山腹间的高速公路,在工程师竭力设计下,剔除了蜿蜒,保留纵深,更加紧密直率地连接着我们思念的源头。
柏油路面漆黑,路基嶙峋的石上爬满青苔,前方高大的落叶树,青翠葱郁渐退,老态呈露,头顶偶尔飞过的鸟鸣声嘶哑苍老沉浑,流进车内的尘粉,也是带着古早气味。我们车上人的情感,和周遭一样,也是旧的,陈旧得如这片红土地上二百多岁的“三美楼”古宅般沧桑醇厚。
陈旧的“三美楼”和其他老物一样地充满了神性,拴住曾被它遮挡包裹过老老少少游子们孜孜不倦的思念。于是,在这些个空闲日子里,近的福州、厦门、漳州的来了,三明的也来了远的上海、江西、广东的来了,河南的也来了他(她)带着恋人来了,他(她)带着爱人来了,他(她)带着儿孙来了,孑然一身的他(她)也来了
搞科研的来了,任公职的来了,经商的来了,务工的也来了
车轮脱离了高速公路后,乡间公路与小溪并行,蜿蜒又神气活现地恢复了。溪水在秋日阳光的映照下,粼粼的白光有些刺眼,哗哗啦啦的流淌声已被来往的隆隆汽车声给掩盖下去了。斗不过汽车,就逗一下河床边上的小草吧。顽劣惯了的小溪水脾性不改,那些贪水外探的水草,被时疾时缓的溪水调戏得时而低头哈腰,时而左摆右晃。
白鹇和乌鸦们,高傲地立乌桕树枝头上,对周遭的喧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是啊!在这丰硕的季节,它们只要稍稍扇开翅膀,潇洒地俯冲到橙黄的原野,轻轻松松就能夺得个撑肠拄肚。
这一黑一白二鸟,白的耀眼,黑的夺目,色调亘古绵远,和老宅一样的隽永极致。
乡间小路的转弯尽头的小溪面特别的开阔,溪岸也跟着宽厚起来,根广又深的绿竹丛与杨柳便在此安居乐业起来,充足的水分让它们衣食无忧,营养丰富。故此,它们枝叶挨挨挤挤,交错在了一起。
二者虽都是同色调,但性格迥异,绿竹显得贪心没有气度,向上,它趾高气昂,拼命地钻。向外,它横冲直撞,拼命地摊占。
杨柳就低调得多了,它向上才一会,就低垂下身段,谦卑地俯视抚慰大地母亲,瘦削的身子,还紧紧地束着,生怕碰着伤到了绿竹似的。
在绿竹与杨柳随风摇曳的对面,就是爱人家族开枝散叶的三美楼。绿竹与杨柳的一张一弛,一收一缩,便是它门前的风景。
随着散处各路人马陆陆续续奔驰到来,原本偌大空荡的三美楼,满了起来,也鲜活了起来。
回到三美楼,我的身份竟复杂多样了起来,楼内的人儿,晃动着的笑靥,时而有人叫我姐夫,时而有人呼我姑丈,时而有人喊我姨丈,这还真有些让我有些应接不暇。
三美楼里的炊烟一改往日的时序,晨至午连续袅袅升腾,柴灶上的铁锅里的祭供由红变白。三美楼的缔造者谢裕韬栖息在那高岗的泥穴中,寂寞地等待着嫡孙们一年一度的缅怀朝拜。
秋日阳光从树林竹海里穿插下来,铺满杂草和黄土织就的陡峭的山间小路。我们的声响在斑驳的光影里穿梭,落叶在风中留恋地挣扎翻滚。
越往上走,竹树越来越疏朗,失去了阻力的阳光,肆无忌惮起来,变本加厉地刺在我们身上,不见鲜血,却把人体内流淌的液汁一滴滴地捏挤出来,着着实实体现着它的威力。
山间天空
饱受这厉害阳光蹂躏的谢裕韬先祖还深知,日光和月夜组合在一起,便不再是平凡的时光,而是一把无所不在、攻无不破的厉害刻刀,而人,在它面前永远是那么渺小与无奈。
可谢裕韬还是强健而睿智的,他认为人在时光面前可以渺小,可以无奈,但作为万物之主,是不能畏惧与无为的,要抗争,要伟大。于是,在稻谷溢出仓,铜板满筐的那一年秋天,他践行了,他抗争了——建一座屹立在时光里的城——三美楼。
石匠来了,泥匠来了,木匠来了,他们聚拢在一起,不再是单打独斗的“匠”,是一个荣辱与共的合体。接着,石头来了,沙土来了,木头来了,它们来自异地,却目标一致,团结紧密。
如沙土本来是分崩离析的,在糯米和石灰的撮合下,不再是纯粹的沙和土,而是牢不可破的“三合土”。
想到这“三合土”它们这样不离不斥,拧成一块的精气神,我觉得它很值得我们如今的一些团队、组织的学习效仿。
石、泥、木匠们在一千多个日夜里,丁零当啷地敲打弹奏,一七九六年秋天的一个夜晚,丁零当啷的乐曲戛然而止。山脚下溪岸边,晨曦雾霭中,立起了一座楼。
好马配好鞍,好楼也得配个好名呀。这个当然是谢裕韬所要思量的,可这并不是一件轻松活,耗神而劳心。当他想到父辈三兄弟名字中都有一个“美”的时候,如卸下了心中的一块石头般轻松,释怀满足地笑了。
从此,三美楼便进入了与时光、与人祸不屈不挠抗争的峥嵘岁月,在那时代和环境并不单纯平坦的岁月里,它先后经历土匪的袭扰和战火的洗礼,至今安然耸立,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主人智慧与顽强的结果。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现今,二楼有两户年轻的主人住在里边,在古旧的大环境里,他们改造自己居住的那一小部分,木质门窗成了扎眼的铝合金玻璃,推合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特别刺耳。
这些现代的东西看上去非常滑稽,犹如古旧的衣裤上缝了一块崭新的补丁。可我并笑不出来,心中却隐隐地疼着。
三美楼不仅庇护着男女老幼,还孵化出几十位分门别类学位、职称的学子,其中最高的一个职称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院士培育出许许多多的水稻品种,让田野里多产出了够全国人民敞开肚皮踏踏实实地吃上一年以上的粮食。它自己的通体却被时光的刻刀刻下二百多刀,躯体锈色斑斑,仍不屈地泛出金黄本色的光,角落阴湿的围墙上杂草挺立,让我触摸到了老宅的苍老寂寥。
于是,离开它的日子里,我思念和牵挂的情感就会饱满丰富起来。久了,发酵成了不安,如此之感念,我虽没有问及爱人和老泰山,但每次到来,他们脸上的喜兴之色,已经告诉了我答案。
正午的天空上,一片白云,停下匆匆的脚步,不再流动,悠悠地躺在老宅的天井之上,恬淡安然。哦!它是生怕发出“呼啦”的脚步声,惊扰了三美楼里欢乐的我们吧。
天井上空
其实老宅内,早已欢腾一片了,白云下的天井里,摆上了筵席,欢乐声填满了三美楼的缝缝隙隙,古宅在这节庆的日子里又焕发出了往昔的风。
但随着期的消耗,古宅许多人又要回归于外出谋生,昔日不少的年轻主人恍若游客。因此,古宅这旺盛的气象总是被萧索长时间地占据,它曾经的灿烂繁华,也已经消失在苍茫而无奈的岁月之外。
当我们转身告别古宅三美楼时,几个儿童在门廊前无忧无虑地嬉闹玩乐,脸上的笑容如开放的花朵般绚丽鲜活,这和古宅古旧斑驳的门墙相映成趣。
刹那间,眼前动与静之间的兴与衰、传承与消逝、维持与改变的比照异常鲜明,长驱直入地击打我的心扉,让我心潮起伏,有一股紧迫的使命感也随之涌了上来。
于是,挥手间,我猛然体味到“常回来看看”的深重殷切,以至镂骨铭心。
[免责声明]本文来源于网络,不代表本站立场,如转载内容涉及版权等问题,请联系邮箱:83115484@qq.com,我们会予以删除相关文章,保证您的权利。